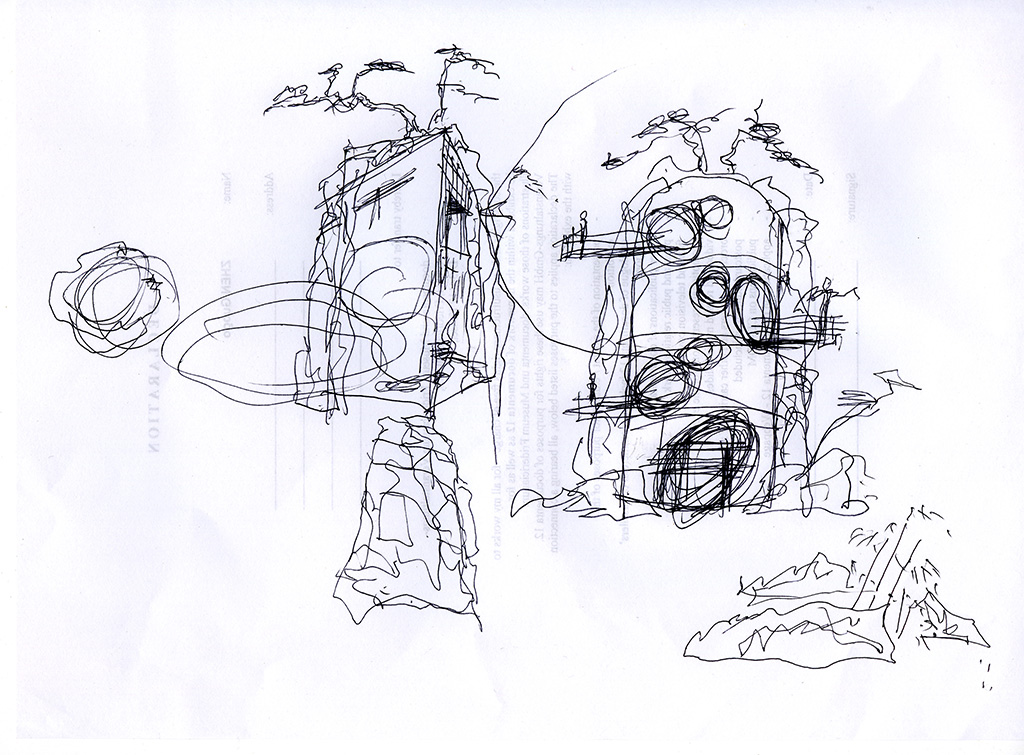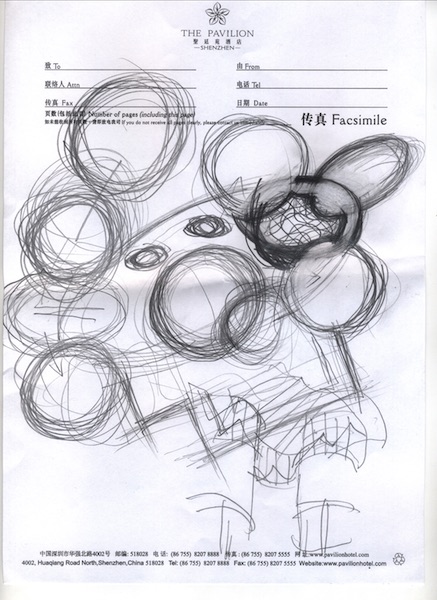从帝国时代到了园
2000年,郑国谷在他的家乡阳江城郊遭遇了一片5000平方米的土地,到2005年他开始他的“帝国时代”建设时,那块土地已经增加到2万多平方米,在接下来的几年,那片名叫“帝国时代”的土地一直在“扩张”中。他为“帝国时代”挖河造山,种树植屋,就像《帝国时代》这个电脑游戏一样,但现实中的”帝国时代”融合了更为复杂的空间形态和社会关系,它不是在特定场所的景观性作品,而是延伸到真实的生活情境里的项目,包容了一个空间从理想到实现以及在生活中持续的全部过程。从2013年开始,他将“帝国时代”改名为“了园”,名字虽改,“了园”还将继续和其前身“帝国时代”的未了之缘,但已蕴含了新的能量学的意韵。以下关于“帝国时代”和“了园”的对话,分别发生于2006年和2014。
“帝国时代”的建造没有施工图,所有的想法都是由郑国谷在随手可得的便条纸上画下来,逐渐形成空间的整体。图片惠允:艺术家和维他命空间。
第一部分:“了园”前身
胡昉:从《寄生建筑》中的违章商品房(2001-2003),到《帝国时代》,你似乎一直在现实空间里为你的能量寻找一个转换的渠道。
郑国谷:在“帝国”里面,我觉得建筑还是一个个人问题吧,要在建造过程中,才能打通个人的秘密通道,可能我必须做一座山才知道那座山上可以长出什么东西。
胡昉:做与不做是很不一样的。
郑国谷:对,从以前小小的越轨吧,到现在这么大的建筑,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像游击战。
胡昉:“帝国时代”反映了一个整体的社会政治空间,实际上也结合了你很多个人体验性的东西,像工作室里的柱子能反映你对被炸拆的阳江人民礼堂的记忆。
郑国谷:虽然那个柱子不一定要那么做,但是柱子的形态一做出来,那个记忆就在了,虽然现实的建筑消失了,但它某些片断的东西又在我那里重现出来。
“帝国时代”的风景,2008-2009年间。
胡昉:我记得“帝国时代”是一个电脑游戏的名字,你一度很沉迷。
郑国谷:我在“帝国”里建造的“奇观”和“帝国时代”电脑游戏里的是不一样的,我是根据需要建造一个“奇观”,但是游戏里的“奇观”是有一个定式的。
胡昉:在游戏中的“奇观”是指什么?
郑国谷:在游戏里面“奇观”是没有意义的,只是一种显示,到了一定时候,它算是文化、财力或者国家鼎盛的展示,每个国家都有的,在电脑游戏里中国的“奇观”就是一个大的天坛。我在“帝国”里的“奇观”还是跟游戏一样,是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的地方,但我把它和一个小型美术馆结合起来。我是先有了这个意识,但以后怎么运用我也不知道,盖好了再看。
胡昉:和虚拟的空间相比,现实中的空间建造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郑国谷:建“帝国”,是对游戏的兴趣跟我现在要解决的建筑问题结合起来,还是活在一个游戏的世界里面。但和电脑游戏不同,虚拟就是一种玩嘛,没有压力的,熬了一个通宵就去睡了,但是在现实里面更惨,你要面对现实的压力,怎么找钱,怎么请人,结构找谁,怎么铺路啊,怎么挖河啊,怎么把石头调过来,这都是要花人力物力,20多吨的石头放哪里我都要确认,还有现实中的各种手续要办,但在我建造的过程中始终有新的东西会出来。
胡昉:对你来说来自现实的压力是更有刺激性的,就把生活本身当游戏。
郑国谷:这个游戏过程中,社会上的交往都显露出来了,或者说让我知道一点点吧。在电脑里面你根本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只是你怎么把它玩好,被打死了也无所谓,找不到金矿也无所谓,重新玩一遍可能会更好。
胡昉:我感兴趣的是你在“帝国”里种植的想法,即你不满足于一种空间转换,而是进行空间植入,这种植入,立刻会连带出它的社会文化情境,不断形成你再次创作的动力。
郑国谷:我要非转农,或者是新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笑)。“帝国”是一个时代,总会消失,但它保留了从违章到合法的所有印记,始终会保留的,没有问题。
第二部分:“了园”今世
胡昉:从“帝国时代”到今天的“了园”,是什么样的一种来自宇宙的力量导致了改名?
郑国谷: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关注这个项目,就会发现里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后来发现所有的这些问题,在那个时间段里,可能会由它的名字的震动波带来,比如叫“帝国时代”,大家都这么称呼的话,就会有一个震动,这是声音的奥秘吧。声音一震动,它其实就是一种意愿,它会让你走向那个声音所带来的那个结果。“帝国时代”这个游戏它也已经衰落了,它被一种新的东西代替了,或者是网络上更有意思的一些游戏。我觉得我那个地方也该有一个新的名字代替它,这个名字我也想了好久。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原来在“帝国时代”的核心,有一个园就叫“了园”,这是我以前一直想做的一个比较核心的部分。其实你把整个“帝国时代”最后的核心一连贯的话,它也就是“完成了”的意思,所以我就干脆用“了园”来代替“帝国时代”。
胡昉:你说的核心是指建筑的核心,还是想法的核心?
郑国谷:刚好那个建筑群里最中心的地方,那不是有一个园吗?那个地方像印度的瑜伽中心,它的那个建筑就是封闭起来在里面练瑜伽的,他们说在里面可以达到能量回旋,其实是每个人的能量在那里积聚回旋。我把它做成圆的庭院,露天的。这个地方做出来之后,有点像一个灵感地,每个人去到那里会产生新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园的这种能量,作为整体的一个核心。
胡昉:你说的核心部分实际上是一个空?
郑国谷:对,就是中空的一个庭院。
了园,2014/2016。
胡昉:所以说与其说它是一个实体,还不如说它是一个虚的地方。
郑国谷:在这个虚的里面,你往上看,那个云,我们拍图片的话,像一个球,像地球,所以很奇怪,你觉得它空,中空的东西你拍它,就是一个很实在的球体。
胡昉:上次我们也曾近谈到虚实空间的关系,“了园”更多地引向对能量空间的关注,这是否跟你说过的从符号学到能量学的转换有关?
郑国谷:这个有啊,比如“了园”这个文字,就暗藏了一个能量的组合。中国文字的发明,是先有灵性上的东西,人对文字要有灵感然后再就有逻辑。它应该有多少笔画?它的空间是怎么样的?汉字它有空间嘛,就像东西南北一样,因为它是模仿了自然的道理,然后它最后呈现的是一个形态,是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每个字和每个字组合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磁场。一段文字,或一篇文章,也都有它的磁场的,这种拼图文字的拼法,最终是以能量来决定这个符号的。
胡昉:这会不会带给你不一样建构空间的方式?你是怎么样看它会改变实体空间的建构?
郑国谷:“了园”其实就是由我之前“帝国时代”的那个中空的空间发挥出来的,从那个空间,我开始知道磁场对人真正的意义,每个人在那里都有同样的反应。在那里我就发现,土地跟人的关系,就是我真正理解了人地关系,再往上看,我们就发现有一种天人关系,但天人关系太深奥了,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对我们来说,我们先要找到这种人和地的关系,我们怎么能够和这个土地的力量成为一体,让它带着我们振动,就你坐在那里就可以了,你坐在那里慢慢你觉得舒服,慢慢你就觉得跟土地的共振是同一个频率。所以在那块土地上,我会用自己的身体去感知,在一个地方蹲几天或者蹲很久,不断地测试它怎么样,在不断测试中,有一种恍然大悟,原来中国的地是有穴位的,穴位其实就在能量的中心,隐藏在这个土地的能量中心,对应我们的人体,土地的穴位要是跟人的穴位对应的话,就会有同一个频率振动,所以要找到一个人地的对应,它就是一个简版的宇宙。宇宙什么都没有嘛,就是一个频率或是一个振动,是没有符号的那个版本,回到能量的版本。除了有形的现象之外的一种无形的力量,我想应该是在现今这个“了园”要捕捉到的比较本质的一些东西。
胡昉:你曾提到过这个项目是你“个人的建筑理想”……⋯⋯⋯⋯
郑国谷: 2000年我从我生活的城市阳江郊区的农民手里购买了一块土地,2005年开始建造我个人的建筑理想,我个人的建筑理想,是视一切为建构。这种建构使一个艺术家要有作为农民一样的定力,这种定力使一个艺术家的意识被深深地刻录在这块土地里,就像农民种的种子一样在大自然里生根发芽,开花到结果,从简单的维度向复杂的维度发展,生长出了房子、池塘、河流,园林景观,在自然环境里生长出了不同的镜像不同的空间。
真正的建构是从藏在心灵的深处折射出来的世界,真正自然是不加任何判断,这个世界也和自然同频,既可向内收缩,又可向外扩张。
耕种与建筑的建构同样是在野外工作,景观的建造与时节有关,是对时机的把握。播种一颗种子,一个维度,把它撒到土地里就是维度开始和空间发生关系,每一个维度都是一个存在,都是能量,能量就是频率的振动,频率的振动与人的脉络相连,用频率去测试空间的功能是最准的,它让我们从符号学走向了能量学。“了园”里面的空间功能与布局是我用身体长时间不断测试出来的。身体的体感功能在建造的环境里舒不舒服,人天感应,是中国古建筑的核心思想,到现在看中国古园林的设计还是能量很大,用脉络去对应它测试它,只要是与宇宙是同频的,气很长,所以运也很长。
了园,2017。
文字:胡昉
文字©2020作者和观心亭
郑国谷作品©艺术家
图片惠允: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