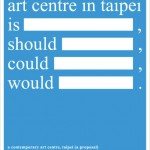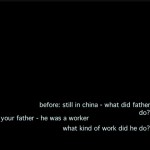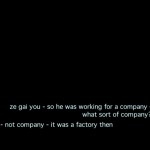为了记忆的遗忘,为了到达的离开
胡昉
姓名
 Jun Yang and Soldier Woods, 2002,DVD,约9分钟.
Jun Yang and Soldier Woods, 2002,DVD,约9分钟.
my name is
Jun Yang /’d║u:n i^n/
Jun is the first name
Yang the family name
in chinese – to be precise in mandarin chinese – it is pronounced
jan chuen /i^n ‘t║u:n/
family name first
my parents on the other hand
are from a region with a different dialect
so when they named me they had a different pronunciation in mind
they would say
Ji chuan /ji: ‘t║u-an/
again family name first
…
we left the country when i was 4
and therefore – in some ways we also left this language (注1)
杨俊,Jun Yang, 中国浙江出生,四年时随父母移民欧洲,在奥地利维也纳长大。
多年之后,他在一个名为《杨俊和杨军(Jun Yang and Soldier Woods)》(2002)的录像作品中,诙谐地描述了Jun Yang这个名字在不同社会文化中所带来的各种“误读”,以及他在这种“误读”中成长的经验和困惑。
正是名字的“误读”,使他发现了个人意识在社会文化中的构建过程,而当代艺术创作,成为他重新建构自身与外界关系的一种媒介。
我们也可以说,影像创作让杨俊发现了一个作为叙述者的“杨俊”,“他”只存在于影像中,拥有和在现实中的杨俊后者不一样的生命。
中国餐厅
 回家-日常生活结构,2000, 录像,16分钟
回家-日常生活结构,2000, 录像,16分钟
 “回家——日常生活结构”装置(2000),由艺术家定制桌子,椅子,海外中国餐厅常用的天花以及录像构成。
“回家——日常生活结构”装置(2000),由艺术家定制桌子,椅子,海外中国餐厅常用的天花以及录像构成。
中国餐厅和杨俊的成长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在维也纳的住宅就在他父母开的餐厅楼上,远远就能看到“天津饭店”的招牌,蓝底白字老宋体颇有中国三、十四年代的那种感觉,有一点点时空错乱。
在《回家-日常生活结构(Coming Home-Daily Structures of Life)》(2006年)一片中, “我”讲述了在中国餐厅里成长的生活过程,叙述者的声音始终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画面淡出淡入的则是好莱坞商业影片中和中国餐厅的相关场面。
“我”讲述的几乎是那一代中国移民在1970年代的普遍经历,开餐厅不是因为他们的专业是厨师,而是求生的需要,因而,富有幽默意味地,是求生的需要促使他们发明出自己的专业,一开始是临时的,随着日常过程,它成为一种有别于西方生活系统的新的日常生活结构,与此同时,餐厅成为家族空间的延伸,成为客厅、厨房、书房,进而,它将对故乡的记忆转换成和所处现实的对话,“家”的意义由此游移出稳固的社会系统之外。
而对从小在中国餐厅里成长起来的“我”来说,“吃什么,怎么吃”的问题,将成为他体察自身与西方社会的一个接口:意识形态的偏见将在“胃”的面前受到质疑。
在这种相互的位移中,一个新的生存空间出现了。
X
 伪装——看上去像他们,听上去像他们,2002-04,录像,15 分钟,录像截图
伪装——看上去像他们,听上去像他们,2002-04,录像,15 分钟,录像截图
杨俊的影像作品,往往是从一个主人公的“自述”出发,类似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这个“我”既可以是故事的主人公,像《关于遗忘与记忆的一则短篇(A Short Story on Forgetting and Remembering)(2007年)中的独白;也可以是一个旁观的叙述者,如《伪装——看上去像他们,听上去像他们(Camouflage – Look like them – Talk like them)》(2002—2004年)中的旁白。而所谓的“叙述者的声音”,往往是在人物自身的性格和杨峻作为影像作者所持有的批评性声音之间微妙地滑动,因此,“我”的叙述的展开过程中往往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经验呈现。
在《伪装——看上去像他们,听上去像他们》中,叙述者向我们讲述了X——一个非法中国移民——的典型故事:X历尽千辛苦,来到异国他乡,他不懂外语,无法融入社会,尽管小心翼翼,还是被抓进警局,他绝过食,渴望大赦;X认识到,只有适应环境,消失在当地人群中,成为大众的一员,那才是安全的出路——对于他来说,语言和衣服一样,具有掩护的功能,求生的意义。叙述者在平静的讲述中,发现了这个社会的深刻矛盾:为了求生而必须让自我消失。
在这个录像作品中,杨俊发展出一种融合新闻剪报、静照、日常生活场景纪录的影
像叙事风格,特别是探索了旁白和影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由此充分展开了影像叙事的空间张力,不事张扬,而又得以层层深入,入木三分。
黑屏
在《回家——日常生活结构》中,杨俊开始有意识使用大量的黑屏,经常,画外音在继续,那些来自好莱坞电影中的关于中国餐厅的画面淡出之后,是大段的黑屏;而那些影像,大多是反映中国餐厅的霓虹灯招牌和餐厅内具有“亚洲”情调的画面,而黑屏正好是光鲜的反面。
黑屏的持续似乎构成了内在的静默和悬置,“我”所讲述的正好存在于画面淡出淡入的黑屏之中。“我”对好莱坞的影像意识形态保持沉默并通过自己的叙述将之悬置。
夜色中的霓虹灯
 关于遗忘与记忆的一则短篇,2007, 16mm胶片, 20分钟
关于遗忘与记忆的一则短篇,2007, 16mm胶片, 20分钟
充斥亚洲都市夜空的霓虹灯,是现代性在城市空间最具魅惑力的书写,从亚洲进入现代性的过程开始,每个都市都在用霓虹灯塑造着自己新的形象。霓虹灯:灯光和媒体的完美结合,而夜空中的霓虹灯,启动了与白天全然不同的都市美学:过渡的、临时的、刺激的、妖曳的。它陡然创造出一个白天与黑暗之间的人工视像区域,反复不断地诉说着、强调着形象的力量。
这个患着失眠症的年轻主人公在夜色中的台北游荡,他爬上楼台,坐在霓虹灯牌下;他穿过布满日光灯的通道,走进24小时便利店。黑夜似乎有助于他梳理他的过去,他的家族的过去,这个城市的过去。
意识如同在蚕茧之中。
在台北的夜色中,他继续穿行于不同的空间,慢慢地,人们发现他的行走路线似乎暗合了台北的都市空间演变和政局分布;同时,他也在回忆和行走的感受中发现自己的家族和这个城市的秘密:一个被不同世代涌入的移民重新书写历史的城市,一个为了满足人们需要和梦想而一再被重新创造的空间,在那儿,真实和想象的边界如此模糊,就像夜色中的霓虹灯。
《关于记忆与遗忘的一则短篇》是杨俊慢慢将自己生活中心从欧洲回到亚洲之后的第一个短片,主人公的活动全部发生在黑夜之中。杨俊在杨德昌、蔡明亮、王家卫等导演的电影中,发现了他称之为亚洲都市“夜晚美学”的要素,应因这种电影美学,他采用16mm胶片拍摄这个电影。但是,在他的镜头下,“夜晚美学”成为一个更为概念化的“潜结构”,来衬托出一个幽暗的历史空白区域,而他所真正有兴趣的也是在电影和当代艺术的影像创作之间寻找一个中间性的区域:在那儿,影像有可能发生流变,观者有可能进入到一个未被触及到的区域:犹如在城市的夜色中,你会发现白天无法发现的秘密。
局外人
 巴黎症 (Paris Syndrome), 2007/08, 16:9 数码影像,10分钟
巴黎症 (Paris Syndrome), 2007/08, 16:9 数码影像,10分钟
杨俊影片中的叙述者,经常是一个主动将自己放逐在边缘的沉思者,从对周遭的观察
和自身的遭遇,不断的反问自身。
他希望从周围隐身;
如果欧洲不是他的家,中国不是他的家,那么他的家在哪里?
他无法确定自己,也不想成为他人;
他无法确定真实的时间;
他从小就没有偶像;
他看到一个表面富裕的全球社会,却充满不确定的身份焦虑;
他的位置,只有通过叙述——一种隐喻性的求生活动,才能反观出来;而影像创作的过程,无疑成为他穿越现实的表层,捕捉生存动力的过程。而所有这一切,暗含着人类生存处境中固有的“梦想”和“希望”。
更好的明天
 更好的明天,2006,利物浦双年展展览现场(2006)
更好的明天,2006,利物浦双年展展览现场(2006)
我们总是生活在关于生活的各种梦想中(梦想总是带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的痕迹),而当梦想和现实相遇的那一刻,具体地来说,是当梦想和现实发生冲突而寻找解决、寻找释放的那一刻,是杨俊特别为之着迷的一刻。
《巴黎症(Paris Syndrome)》(2007)是关于广州欧陆风情居住小区的一部建筑学笔记,那些小区拷贝着各式欧陆的建筑风格,从意大利、西班牙到德国的、瑞士的,中国的现实和中国式的实用主义又使得居住其间的人们赋予她们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使用方式,在影片中,一对造型现代但又略嫌造作的上班族男女,在这些空间里走动。杨俊的兴趣并不在于进行简单的批判,而是在于发掘这些建筑背后的人心所向,如果说,Copy是对某种真的东西的追求,那么,在copy里面表达的也是一种渴望,一种关于梦想和现实的关系,虽然这个现实已经被过多的欲望悬置了起来。
《更好的明天(A Better Tomorrow)》(2006年)因应利物浦双年展而作,场景移到了利物浦,但影片延续了杨俊对城市作为人类理想生活的“展望空间”的研究。主人公的叙述再次从父母的故事讲起,这次,从叙述的一开始,主人公的父母离开了“这儿”(利物浦),回到了故乡,似乎当初父母在“这儿”落脚时,就是为了能更好的回到他们当初逃离的地方,主人公面对如何处理父母离开后所留下来的生活物件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发现了永恒的时空错位:他们的今天是为了更好的明天,尽管“明天”的景像一再延迟,关于未来的乌托邦一再失落,但正是那种永恒的“待机状态”,推动着他的父母,这儿的人们,这个城市,不断进行着自己的转换。
在某种意义上,“更好的明天”这个标题本身就暗含了生存的悖论:它无疑是政治家和地产商们最热衷的宣传口号,但也完全可以从它通常意义上的广告宣传口径上抽离出来,而重新让我们正视和承认这个生活的基本事实:我们都有生活在“更好的明天”的希望、责任、权利和义务。
在他为这个影片所作的装置中,“更好的明天”以霓虹灯的形式,在一个盖了一半的屋子上方闪亮。
阳光中的森林
 挪威的森林,2008,16mm胶片,18分钟
挪威的森林,2008,16mm胶片,18分钟
和《明天会更好》的故事相呼应,《挪威的森林(Norwegian Woods)》(2008年)中的女主人也面对着要处理父母遗留下来的物件:她从城市坐渡船回到小岛,回到小时候的老屋子,而她面对的是处理母亲的遗物。
这是杨俊第一部有对白的“故事短片”。
场景取之于挪威北部位于北极圈内的lofoten群岛,那儿的自然光线具有迷人的气质,似乎有意强调它与《一则关于遗忘与记忆的短篇》中所呈现的亚洲都市“夜晚美学”的反差,这部片子完全采用白天的自然光拍摄。
在这个影片中,画面切换之间出现的是蓝色,然后镜头拉远,这是蓝天或海水的颜色。
当《明天会更好》的主人公在整理父母留在旧屋的杂物,思考他们为什么离开这个城市时,《挪威的森林》的女主人公也许正在北极圈的光线中仔细整理母亲的遗物,有趣的是,他们都采取了同样的决定:只保留了少量的照片、书籍和物件,而将剩下的东西散布在城市不同的地方。
她把衣服放在了小镇的慈善机构前,书给了图书馆,录音机留在了垃圾站。
在她离家之前,举行了一次聚会,多年不见的朋友把酒言欢,互相分享记忆。
藉由分享、转移、错位、转换,对某人、某物、某个城市、某个国家、某种文化、某块土地、某段历史的记忆得以永存,并重新创造出新的空间。
这个过程如日夜流转,永恒流动,而杨俊影片中沉思、孤独、敏感而又隐忍,有时又是异常雄辩的叙述者将陪伴着我们一起看到世界运转的光晕。
她离开小岛的那天,阳光灿烂,她在阳台上远远望见一个年轻女孩穿着她母亲的裙子,在十字路口匆匆而过。
(图片提供: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文字提供:维他命文献库
















![Jun Yang wiener[00_04_32][20130509-195413-3]](http://vitamincreativespace.com/cn/wp-content/uploads/2013/05/Jun-Yang-wiener00_04_3220130509-195413-3-150x150.jpg)